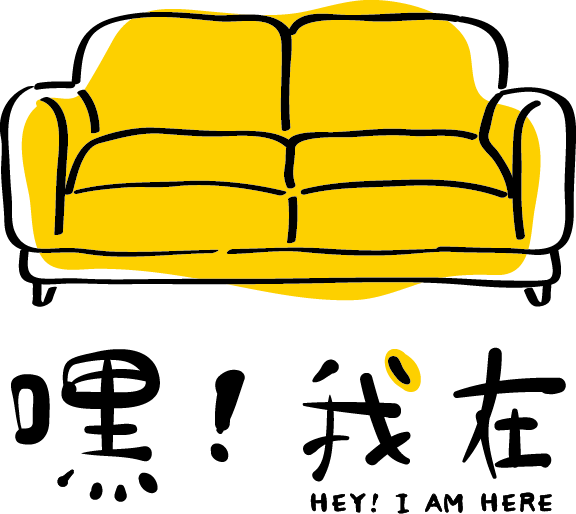情關難過,大抵就是我的情感生活寫照。
從小到大,總是遇上「我喜歡的人不喜歡我,喜歡我的人我不喜歡」的劇本,看了再多兩性文章也還是化解不了心裡的對愛情的迷惘、渴望和……害怕。對,害怕。太多一樣的情境重演後,我開始不敢相信自己的「感覺」,每一次跟人相處得很好,或對方特別照顧自己時,我都要強制啟動心裡的警報系統,不停提醒自己:一定是你又自作多情了,你既不漂亮又不特別,在那邊自以為什麼……心裡的警報盡力地用貶低自己來強迫自己漠視喜歡一個人的情感。
但,誰不渴望愛情?警報系統總有一天要崩潰失效。
2015年,我喜歡上一個從沒想過的人。那些曖昧朦朧的眉來眼去,身體熱烈的撫摸接觸,無話不談到天明,時不時的眼神溝通與默契,都讓警報系統徹底失靈。但,又來了,對方不喜歡我,對方沒有要回應我的認真,對方說無法從獨立的我身上索取他想要的「被需要」。
我們總是用太多問號折磨自己
什麼是被需要?為什麼對方覺得沒有被我需要?那些迷人的微笑都是假的嗎?那些半瞇著眼的擁抱和讚美是什麼?如果不喜歡為什麼這麼有話聊?為什麼都接得到我的哏?那不就是默契和緣份嗎?面對內心無限的困惑,我無法理解;我理智上知道,這是錯的人,離開就對了,但我感性上無法放下心中的喜歡與不甘心;我一邊強求,又一邊不准自己把自尊丟在地上任人踩(雖然最後還是丟了……)
這些糾結,都鎖在心裡。從事創意工作的我,工作時需要高度專注與快速運轉,我無暇也不願意正視自己的低潮和傷心,我不斷用老方法對自己喊話「妳可以堅強一點嗎!」「妳不需要愛情,從小到大愛情給過妳什麼?」「傷心個屁,為這些事這個人流眼淚,有人幫妳擦嗎?」
結果,我靈肉分離了。
看起來沒事,不代表真的沒事
所謂靈肉分離,近似「高功能憂鬱症」,也就是能夠執行日常生活功能,甚至還表現優異不被周圍的人發現低潮的「持續性憂鬱」狀態。儘管,沒有得到精神科醫師的確診,但與後來讀到的病徵非常類似。
高功能憂鬱症可能的症狀與行為:總是很忙、工時極長、感覺很堅強不需要別人、飲食與睡眠失調、難以專注、覺得與他人有距離感、追求完美、自卑、需要花費極大心力才足以維持看似正常的生活、很害怕被拆穿。
那一年,大家看不出來我的內裡早已崩潰;只有要好的朋友知道,我剩一個空殼。
上班的時候,武裝完畢的我,承受高壓的創意工作。盡力在快要當機的腦袋中搜尋 idea,在提案時維持熱情與幽默,把大家共同努力產出的創意賣給客戶,在監拍的時候維持專業,堅持高水準的要求。我用盡力氣,努力跟上大家的談笑,但只有我自己知道,我有多麼皮笑肉不笑,我快樂不起來,我常有眼淚在眼眶裡測試表面張力,我一下班就崩潰,愛面子得要死的我曾經在捷運上不顧一切就哭了起來,不顧妝會花,不顧有人在看。
那段日子,我搬出家裡,因為無法承受家人的關心和詢問。面對爸媽,我不想說,我不知道怎麼解釋,我覺得關心讓我煩也讓我自責,我覺得我連自己都照顧不好很不應該。
時間並不能撫平一切,除非你開始面對和接受自己
在我短租一年的小套房裡,我會躺在床上,聽空調聲,哭,做什麼都哭。一直很愛看書的我,沒有文字活不下去的我,什麼都看不下。喜歡電影到年年買套票泡在台北電影節的我,無法看電影,常常是眼睛看了,卻完全不知道電影在演什麼。曾經覺得一個人睡雙人床爽翻天的我,一個人蜷在床上,覺得床好大,像太平洋那麼大,我覺得很孤單,我覺得我被拋棄了,我覺得全世界只剩下我一個人。
這時候,我養的貓,一隻非常貼心懂人話的橘貓。她會默默跳上雙人床,用額頭撞開我蜷曲閉鎖的身軀,硬把自己全身的溫暖塞進我的胸前,舔我臉上的淚痕。
她讓我心裡總惦記一件事:我要活得比她久,因為她只有我。
很少跟朋友坦露過多低潮情緒的我,開始試圖找人講講話,大家努力撥出時間與和能量接住支離破碎的我,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要過,沒有人能填補所有我的需求。更何況,我心裡清楚明白,我整個人掉進了情緒黑洞,無止境的低潮,沒有盡頭,是百慕達。
就這樣過了至少半年,低潮情緒並沒有像坊間文章所說「時間過去了,就會淡掉了」。我的情況嚴重到,腦袋裡有一句話不停尖叫折磨我:「都是我的錯!」那個頻率近似黑死腔,不分日夜尖叫。
我終於投降了。
從身心科到諮商室,我練習接受幫助
第一次掛了身心科,但我千算萬算沒算到我的武裝並未投降,坐在醫師對面,我冷靜理解又超有條理把我的事情、狀況分析並說明,醫師靜靜聽完,愣住了,掩飾不住滿臉問號,空氣凝結三十秒。
「妳需要我幫妳什麼?」
「我……想睡覺。」
醫師開了極輕量的安眠藥和抗憂鬱藥給我,未料我的體質對藥效太過敏感,雖然睡滿八小時會醒來,但接下來八小時我都像潛潛水似的,同事的話和動作都跟我保持了過遠的距離,我飄忽,我反應遲鈍,我覺得我每天都降落在錯誤的星球上。
我沒有辦法一邊吃藥一邊從事創意工作。這條路走不通,但我沒有放棄求救,為了愛我的人們和愛我的貓,我沒有放棄,我向平日陪伴我的心理師好友詢問了諮商的資訊。
我走進諮商室了。
每次叨叨絮絮像在說著別人的故事,諮商師可能兩小時都插不上一句話,一個月,兩個月,三個月,諮商師越來越懂如何在我說不停的話語中見縫插針,不著痕跡地引導我梳理自己。晤談了幾個月後,諮商師對我提出結案的可能性,我對自己沒有把握,就像不敢信任自己的感覺一樣,我怕我又掉進黑洞,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放掉像是救命索的諮商師。
諮商師帶著溫暖堅定的笑容看著我。
「人生一定有風雨,不可能等到一個只有晴天的世界。」
「之前的妳,需要人陪伴和引導。」
「現在的妳,懂得為自己撐開傘。」
「我們可以嘗試進入下一階段的練習,就像是實習一樣,去實作。」
「如果妳隨時覺得不行了,我們都能再度開啟諮商和對話。」
我不安,但我願意嘗試。
低潮還會再來,但我不是一個人
我恢復了重訓,帶自己去買菜,買喜歡的玉米筍、秋葵、雞胸肉,每天作飯切水果,為自己;每天準備便當,為自己;每天試著笑,為自己;每天讚美,為自己;每天找到一點身邊的小幸福,為自己。
然後,在朋友和貓咪的擁抱中,練習接受「情緒」總會起起伏伏上上下下有高有低,偶有低潮是正常的,不用害怕。練習接受所謂的平衡,是動態的,每天都是新的練習,每天都有新的可能。
曾經從動物溝通師口中得知,我的貓陪伴著我窩在小套房的那一年,她覺得我像是一盞快要熄滅的燭火,她很害怕失去我。
謝謝每一個曾經接住我的人,謝謝給我全部溫暖的我的貓,請妳要健康,請妳陪我再久一點,謝謝只能接受我突如其來搬家決定的爸媽,謝謝邀請我一起創辦《嘿,我在》的小華,謝謝什麼都沒多問就說好一起為《嘿,我在》努力的心理師,我的摯友。謝謝你們讓我知道:我不是一個人。
掉進情緒黑洞兩年半後,我走在自癒的路上,如果正在看文章的你也需要有人同行,請讓《嘿,我在》陪伴你。
Kenya
自由創意接案人,現為《嘿,我在》共同創辦人。關心性別平權,熱愛山與海,曾獲廣告金句獎,也經歷外貌焦慮、飲食障礙與情緒低潮,以及每個人都對自己伸出手的溫暖,和小華、大容許願一起陪伴每一個情緒低潮的人。